币安交易所 Binance jiaoyisuo 分类>>
央视杨君专访原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新闻调查栏目制片人夏骏:告诉Binance 币安 ——比特币、以太币等加密货币交易平台2025你一个真实的夏骏
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钱包,币安app官网下载,币安电脑PC版,币安交易所网址,币安app下载,币安邀请码返佣,币安交易所官方网站下载,币安交易所,币安,币安下载,币安注册,币安交易所网址,币安靠谱吗

1999年开始出版媒体专著《英雄三部曲》(《英雄》、《现在》、《笑容》),由于形象时尚,风度气质俱佳,温和与智慧并存,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被称为央视“智嘴”,国际著名大家金庸为《笑容》亲自写序,对杨君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多次出任中国电影电视发展高级论坛主持人并当选主席,2001年获得“新世纪百名杰出女性”称号,并成为新华社“环球20位最有影响力的世纪女性”仪式上唯一的颁奖嘉宾,影视传播学作品被译为17国语言。
杨君1990年成为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传媒学专业第一位硕士研究生,1992年因品学兼优成绩优异获得国家教委研究生奖学金和三台奖学金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中央电视台工作,以媒体评论员的犀利笔锋撰写大量以媒体为内容的调查及评论,首次提出电影具有媒体属性的观点,同时指出应将媒体的范畴包含八大传播媒介——电视、电影、广播、报纸、杂志、图书、音像、网络等。提出以媒体事件中的典型人物作为研究个例来纵向集纳考察中国及世界媒体发展的观点,并加以成功实践。
“到了这样一个生命阶段,必须有一个特别的度量,一个人有效的生命是有限的,也就是三十到四十这一段,电视需要实践,我出来做也不是件坏事。现在新的一茬人在30多岁开始崛起,如果我换一种模式,我想是一种好的尝试。这一段时间是经常夜里三点钟才醒来,那么多人,那么多制作,每天三个半小时滚动不出问题,供求时间的差距。我们用一年的时间酝酿,没有一个成型的方案,就是要做一个辅助的频道,从业务上讲,你的业务是在前进的。我是86级的研究生,第一届研究生,分配到电视台,比较早的一段时间,如果你换一个角度说我可能是坎坷的,但十年的人生积累为后半辈子做事铺垫一点心理基础,同时也训练了我的很多以前不具备的能力,比如周到,比如平和,比如宽容,再比如对时间的珍惜和对生命的热爱,对父母的关怀。我希望用两年的时间积累再一点人才,积累一点经验。我现在的心态一方面是从容超脱的,一方面是有很大工作压力的。”
在北京广播学院校庆讲话中,北京广播学院副院长任金洲说:“北京广播学院一向被誉为中国广播电视人才的摇篮,40年来,学院文科为全国广播电视系统及相关行业输送毕业生1000多人,培养在职人员2万多人。他们遍布全国各地,有的已成为广播电视厅(台)领导,许多人已成为社会上很有影响的记者、编辑、导演、制片人。比如从事电视新闻制作的有79级摄影专业的袁正明---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主任是《焦点访谈》、《东方时空》的总制片人;《新闻调查》栏目的两任制片人张步冰、夏骏也都毕业于广播学院。
而《新闻调查》的最初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当张洁赴“西古县村”拍摄,夏骏采访“宏志班”的时候,谁也无法告诉他们《新闻调查》该怎么做,只有“调查”二字给予了心照不宣的约定。后来它的第一个节目理念就是“调查理性”,其后依然承继着这一理念,并提出“记者要有调查感”的口号。最后《新闻调查》的本质就是一档以记者的调查为主要方式的电视深度报道节目。调查只是一种手段,只不过是一种较为有效的手段,而《新闻调查》的灵魂在于思想维度的深刻和理性的深刻,调查只是能较好的达到这种深刻的表现途径才有价值。
其实有相当一段时间人们都在议论媒体的话题,有人说由于地方台风风火火的上星运动,以及凤凰卫视成功地直播了诸如香港、澳门回归,国庆50周年等大型活动,央视作为全国惟一的强势媒体的地位不断遭受冲击。是象一些评论所说的“国家台”、“中央台”与“全国性”、“权威性”已开始走到了落花季节吗?其实笔者看来,从遵从世界生物多样性原则和物质多样性原则出发,任何事物存在竞争是正常的,这样有助于事业和社会的进步,而且也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如果没有竞争反而是不正常的。当然这一切都得符合竞争原则和基本规则的。
“2000年的6月1日,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也是我们共同创造了一个节日,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改版开播是银汉传播走向未来发展路上的一个目要项目。6日1日也具有某种象征性,我们和无数孩子们一起度过了紧张而又兴奋的一天,孩子的节日是充满生命力的日子。每个人带着不同的历史走到了一个共同的事业进发点,主持人孙宇在一次夜间聊天时对我说,那一天新目标一出来,他眼里会有泪,一种被新的事业和新的人生可能性激起的冲动激荡着自己,这一天无疑是他生命中的节日。”
“但就我本身而言,你往前冲的道路上,每一次进步都是开阔的,你拥有的资源会越来越多,你拥有的能力会越来越多,只是目标的调整,我出来以后,当你有一个更加广阔的资源、一个更加广阔的田地供你发挥和施展,你的经验越来越丰富,但是谁也不能够说你的目标是不是就永远确定了。你在行走到七百公里的时候,你停下来,因为前面有一些障碍,当你顺着河边绕了一个圈后绕开了障碍,你却发现你现在的目标与原来的不一样了,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也是一个风景。有一个公司叫思科,他的目标就是在发展中不断变化的,最后达到的目标是以前他没有想到的,但是却是一个很大的收获和成功,我们做媒介企业和他们有异曲同工之处。”
中宣部新闻局说,电视市场需要制定的政策,可以探索电视制作多样化的道路,但一定要做好,我们不能等的时间太长。人们相信电视将来的挑战主要来自网络。电视业本身也正经历着由单向广播式向双向交互式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带来的是传输形式的革命性变化。它要求传输的内容、管理也要相应发生变化。对中国来说,电视业的开放是市场和技术迫使电视业做出适应性选择。有些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在进入网络交互时代之前,中国电视业要补的重要一课应是市场化。
“她在我小时候,给我一种很朴素的品质,就是:别人给你一杯水,你要还人一壶水,永远不要占任何人的一种便宜,回报别人要比别人给你的多,是这样一种信条。然后什么事情一定要由善于待人来取得最后的成功。所以我上大学的时候,放寒假回家的时候,我们家过年做的一些过年的食物,她都让我去送给那些孤寡老人。所以我们这个村庄的这些老人,我在北京期间,他们临终的时候还在念叨我,因为我是每年都去给他们送过年的食物,这是我母亲给我的。其实她也是培养我这样一种东西,我自己也愿意去帮助一些弱者和老人,我觉得他们内心这种很深沉的东西——你如果去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他们找到一种寄托,对他们内心是个很大的安慰,而你也很轻易地就做了一件善事,自己也很充实,很高兴。而且只有这样的弱者和很少有人给他关心的人,他才能体会到一份认真的关心是多么有份量。
“因为我父亲是个小学校长,所以从小我们有机会接触一些文化的东西。因为他即便现在看来用一些比较原始的方式来要求他的子女去这样做事情。确实象我们江苏那个环境里,对于文化、通过文化来改变命运是一种共识。在这个情况下,大家都知道,一个孩子没有文化,在未来是没有出息的。他有一种很原始的压力要求你学文化之外,我们其实要说学文化的目的有两个:一方面,你认为你比别的孩子多一些接触文化的、就是说有兴趣,对于文化,尤其是小时候对一些文学,所以一些大视野是些比较少的一些视野,视野并不开阔。只要能接触文学,文学本身跟你自己的感情能形成一种沟通以后,其实很需要陶冶,从内心对他的不满意。就是这样的东西,因为那样的环境和那样的事情,它不属于你,你的事情在哪里,全靠他自己去做。
“事情本身其实也是因为一种很强的国家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这里面有几个理由,一个是我出身农村,我从小见到那么多的父老乡亲的那种艰苦,很苦,由于我自己很小的时候也做一些农活,那时候本身是一种点点缀式的,虽然个人没有很大的压力,但很小的时候和土地就有交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个人的人生起点很低。就是什么是人生的低谷,对我来说低谷还远远没有那么严重。事实上我是一个来自土地上的基础的人,我们的底线就是土地。我们个人所受到的一些委屈、误会,或者我们自己所遭受的压力和困惑,对我们来说依然是我们精神程度上的,远远还没有到我们生存上的底线。这一点就是我们中国这几代人中间有那么多坚毅的力量的来源。”
“我不是钢筋混凝土上长出来的花,我们是土地上长出来的儿子。这样一来可能给我们一个原动力。什么是艰苦呢?咱们的父老乡亲的披星戴月的感觉才是艰苦,那种打农药的季节,因为农药的,尤其是在夏天我们在高温之中打农药,极有可能晕倒的才是艰苦。就是在前几年在我的老家我还听到这样一个事情,打农药的人晕死过去,死掉了,就是因为棉花的病虫害的治理,尤其是夏天中暑了,也由于不能及时治疗死掉了。这是人生的底线,对于我们来说还远远没有达到。所以我们承受的一点苦难,在我看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人生其实在那样的处境里面,收入那么少,也有他很美好的东西。我从小和那些最底层的平民感情很深,我都出来二十年了,二十多年了,我现在回家对我小时候祖母一代的老人,都九十来岁了,八十多岁的人,她们见到我非常亲,我就和它们坐一坐,看看她们被关节炎折磨的腿,和他们说一些家常,聊一聊天。她们非常高兴。土地实质上是一种非常温厚的东西。只要认真地用一种真诚的态度面对土地,他对你就特别忠厚。这种与最地层人的呼应,实质上这是在人类精神历史上是非常宝贵的东西。
“我觉得这几年使我自己获得了一切可能性,我主动地去走了中国149个贫困县,用将近两年的时间,在后几年中重新开始建立新的信心。包括最多的时候我用七十九天去了云贵高原。这样一个过程对我来说非常好,因为它强化了一个真正的中国底线的认识。这个过程对我来讲,就是我系统地获得了对于中国最底层的系统认识。对中国九亿人的底层的认识,包括对中国九亿农民的各种生存状态的认识——穷的、富的,中国的所有的最有名的乡镇企业家都是我曾经采访过的人,接触过的人,曾经在他的村庄中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人。所以让我陆续认识了九亿农民的所有的生存状态,。我还能用一个知识分子的眼光去客观地打量和看待他们,也可以渐离地来看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因为他们是中国人口的主体。这样我把对九亿人的五年时间的考察作为本钱,我为什么要走这样的五年,年轻人所获得的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是仅仅从书本上获得的。而对于这个国家和这个时代发展的真谛,我觉得就在土地上。”
夏骏在1990年做的第一个事情是走了149个县,两年的时间走遍了中国所有的贫困地区——五指山、沂蒙山、井岗山、大别山、塞北、内蒙大草原,走遍了千山万水。然后他做了中国的一百个村庄的节目,叫《乡村中国》。“走了十八个省,选了十六个具有典型代表区域的中国农村点,象温州、石狮、山东农村,象宁夏的贫困地区的农村,走了十八个省的十六点比较深入,每一集是一个点,在一个点上是半个多月,后来又做了我们认为继费孝通之后,他做了《乡土中国》,看五千年来中国文化在中国老百姓现实生活中的活的标本——叫《东方:一个伟大文明的生物学解剖》。在山西的运城和临汾。”
“比如有的人从矿井中出来,很苦,他对生活的忍耐力很强;但从土地出来的人不一样,在哪里呢?他很诗意,因为土地在不断给你各种各样的风景,当一个生命力比较强的人,象我老家那样的江苏的水乡,傍晚的时候,你割了一篮子喂羊的青草,拿着一本书,坐在河边,看着彩霞和落日在河里的落影,后来我一直在回忆那种东西。到我的孩子这一代,他们怎么有这样的福气去感受这样的一种自然和人生的混合,那确实在培养人的感觉,然后来的很多感觉,包括你的时间系统的灵敏。那种水波的感觉。”
“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清明时节,那满地的杨柳和菜花,这是我印象里的诗一样的感觉。人生其实在那样的处境里面,收入那么少,也有他很美好的东西。我从小和那些最底层的平民感情很深,我都出来二十年了,二十多年了,我现在回家对我小时候祖母一代的老人,都九十来岁了,八十多岁的人,她们见到我非常亲,我就和它们坐一坐,看看她们被关节炎折磨的腿,和他们说一些家常,聊一聊天。她们非常高兴。我们骨子里的贫民意识,那就是不断地告诉我,活着,千万不要把自己张狂起来做什么。”
夏竣认为包括中国书斋里的知识分子都没有搞懂,我们孔孟的东西是书籍,但很多人拿中国文化当一个书本的概念,这是有偏差的。“但是在土地上活过来千千万万的人,几百代的人,几千年活过来,他们实际上的价值观和生存方式里为什么能够同传统文化形成一个血肉相连的浑然一体的关联和设计,这种设计是用什么构成的,与书本上的中国文化有怎样的区别和呼应,这是两码事。所以我们做了六集,300分钟,叫《东方:一个伟大文明的生物学解刨》。想做一个细胞,他的生老病死的过程,关键是怎样设计自己的生老病死。为什么,一个孩子满月的时候有那样大的一个盛典?为什么一个老人去世的时候,即使是一个贫穷的家庭,也有象盛宴一样包装它?为什么这个农民对计划生育没有儿孙感到是那样的痛苦?为什么中国人用士、农、工、商这样一个价值观来认识来取舍自己的命运?这是一个记录、分析和解剖。解剖就是看他是怎么一回事,就是把我们的解释和分析也告诉你们。”
夏骏说在这部片子里涉及到一个节日的研究,中国传统上的重大节日在农村的表现形式他都有记录,然而这些节日的文化渊源和存在原因是什么呢?“这些东西是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做为一个节目的项目他已经成为化石一样过去了,但对于自己人生的阅历来讲,这一切成为你的基础。我在五年的时间,我看到的中国土地上的变化是有限的,对于中国底层的人和事带有一份尊重和理解,对于这样一些人群我会很仔细的观察和包容,从此成为我今后做事的很重要的原则。”
从采访农村节目五年回来以后,夏骏开始在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参与创办《新闻调查》栏目。“那时候回来,我已经成为一个思想非常成熟的人了。我也很快地让同事们和领导认识到我是一个可以很客观、清醒、成熟地看待中国的青年人,甚至我要比我的同代人感受要深。这就是五年来我对中国底层九亿农民的生存状态和他们的所思所想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这一点是我一生的本钱。后来在工作中,坐在中央电视台的办公室中我会经常忽然在想,在陡壁上生活的人他们现在是怎么想的?在这样的时代浪潮里他们该如何反馈?黄土高原窑洞里的人现在怎么想?乡镇企业家们他们怎么想?包括他们怎么忧郁、怎么成长?这一切日后成为我后来做事的重要的参照。”
“他们把他们所有的作品拿十六毫米机器放给我看,把他们家里的历史背景和他们之间的关系都告诉我,把我当成一个知心的朋友。我学到了很多。电视史上中国的东西我都看过了,和这批人成为了朋友也加强了我的业务信心,我看到了他们是怎样想问题的——戴维宇、陈汉元、涂国壁、刘效礼、王娴、藏树青这些老纪录片编辑,我们成为了朋友并筹备中国电视编导学会,中国电视需要理论。当时骑着自行车从北京广播学院到复兴门,借钱卖的自行车,年轻的时候真得很有劲儿!穷学生,很不可思议。”
“因为我是学电视新闻的,专业角度还是比较窄,所以通过一个尽量宽泛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积累一种知识的信心,通过获得知识的数量,方方面面的了解,来这样的充实自己。我的一个老师对我影响比较大,他是学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鲁迅的,他研究现代文学史,他给我一个很大的理想,我在大学二年级他就跟我谈过,他说:我可能在你毕业的时候,我呢就做研究生了。当时我那么年轻,我才十八岁嘛!如果在那个阶段能够多念几年书的话,是非常有诱惑力的。这也是我后来上研究生的原因。”
“因为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是个文化、文学的时代。那个时候,我觉得从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这些作家里面,我喜欢读朱自清的东西,朱自清是我的老乡,就实际上我更多的从我的性格当中有一种朱自清这样的一种性格,很清淡、很随和的一个人。象鲁迅那种很滂沱的东西对我非常有鼓惑力,也许是我性格当中有矛盾,我是AB型血,可能这就矛盾,性格矛盾。你比如说鲁迅吧,我是大学二年级18岁的时候的暑假,我就读完了《鲁迅全集》。做了一千七百多张卡片嘛。《鲁迅全集》大概是一个年轻人充满了一种生命的压力的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和一种跟周围世界之间相处之间找感觉的这样的一个年轻人。鲁迅给了我很多的东西,但实际上他给我的东西里边也有跟我个人的性格都不是很吻合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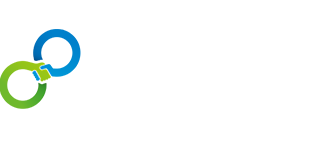
 2025-07-24 08:25:05
2025-07-24 08:25:05 浏览次数: 次
浏览次数: 次 返回列表
返回列表 友情链接:
友情链接:





